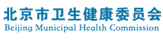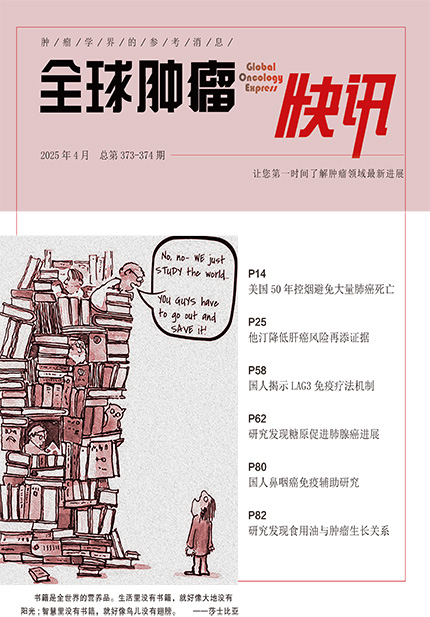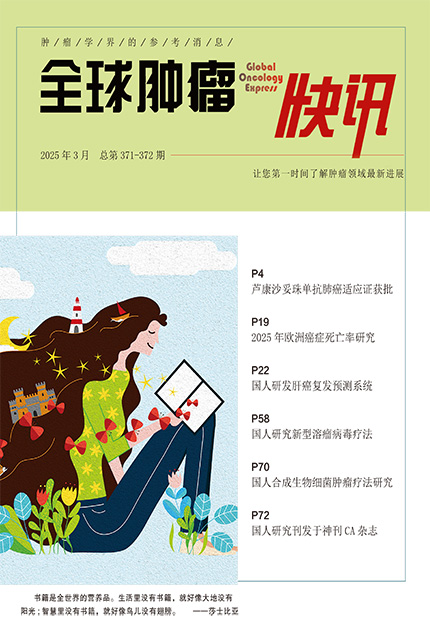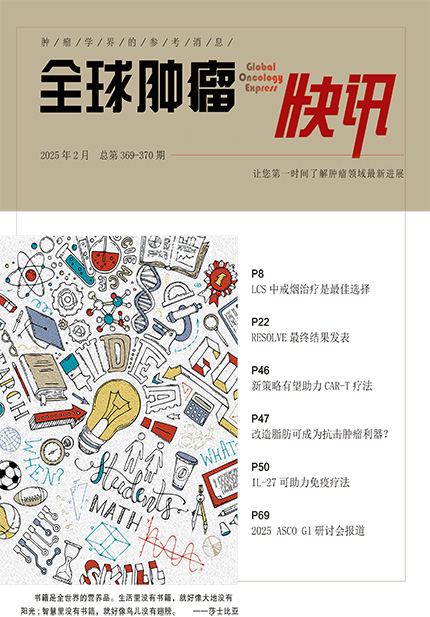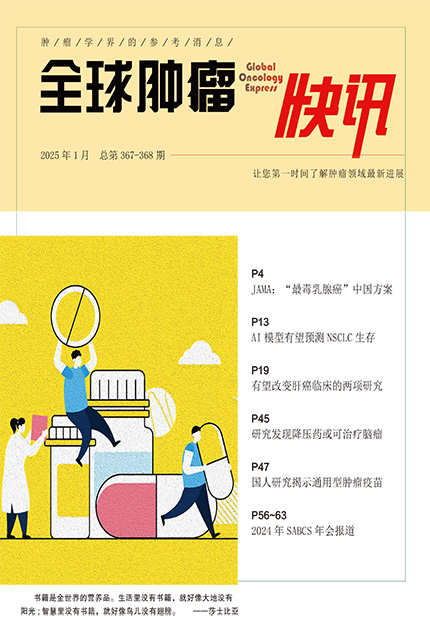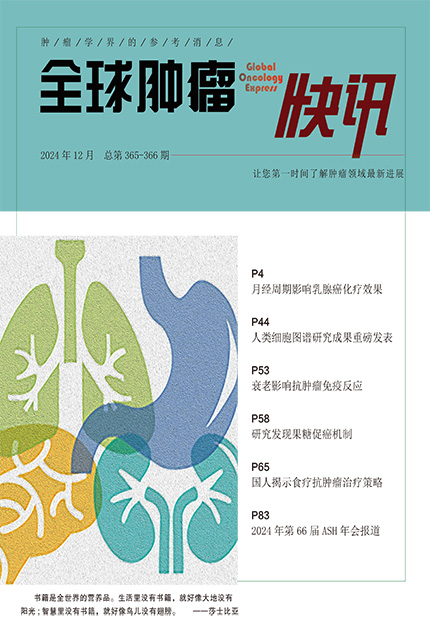- 院所概况
- 就诊服务
-
科室介绍
科室介绍
特色医疗
特色科室
- 胃肠肿瘤中心一病区
- 胃肠肿瘤中心二病区
- 胃肠肿瘤中心三病区
- 胃肠肿瘤中心四病区
- 肝胆胰外一科
- 胸外一科
- 肝胆胰外二科
- 胸外二科
- 乳腺癌预防治疗中心
- 妇科肿瘤科
- 头颈外科
- 骨与软组织肿瘤科
- 泌尿外科
- 家族遗传性肿瘤中心
- 乳腺肿瘤内科
- 胸部肿瘤内一科
- 胸部肿瘤内二科
- 淋巴肿瘤内科
- 消化肿瘤内科
- 黑色素瘤与肉瘤内科
- 泌尿肿瘤内科
- 日间化疗病区
- 中西医结合科暨老年肿瘤科
- 康复科
- 介入治疗科
- 口腔科
- 肿瘤放疗科
- 手术室
- 重症医学科
- 麻醉科
- I期临床病区
- VIP-II
- VIP-Ⅰ
- 移植与免疫治疗病区
- 疼痛门诊
- 肿瘤外科
- 肿瘤内科
- 心内科1
- 肿瘤中医
- 疼痛与睡眠
- 康复中医
- 综合研究型病房
- 职工保健
- 支持治疗科
- 生化与分子生物学研究室
- 病因学研究室
- 遗传学研究室
- 流行病学研究室
- 分子肿瘤学研究室
- 中心实验室
- 临床实验室
- 图书馆
- 实验动物室
- 生物样本库
- 细胞生物学研究室
- 家族遗传性肿瘤中心实验室
- 肿瘤生物信息中心
- 胃肠肿瘤生物学研究室
临床科室医技科室基础科室行政处室 -
专家介绍
专家介绍
-
科普园地
科普园地
疾病专题
健康大讲堂
-

仁医陈敏华 用射频针创造生命艺术 浏览量:3718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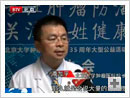
【北京您早】恶性肿瘤成北京市民头号杀手 浏览量:1683
-

【生活大调查】终结癌症传言 浏览量:2730
科普园地
防治雾霾
健康自测
-
食管癌切除术后生存预测
| 北京市重点肿瘤高危人群自我评…
| 疲劳度自测
| 便秘自测
| 自己检查胃肠病
癌症康复杂志
《癌症康复》分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癌症康复总论,主要介绍了癌症病人的心理调整、饮食营养、心身锻炼、生活指导等基本的康复知识、技能和方法。
综合资讯
-
- 招聘动态
-
院务公开
院务公开
-
院刊杂志
院刊杂志
Chinese Journal of Cancer Research
The Chinese Journal of Cancer Research publishes high-quality original articles reporting new information on basic and clinical aspects of cancer research and related subjects.
全球肿瘤快讯
院报专栏
癌症康复杂志
《癌症康复》分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癌症康复总论,主要介绍了癌症病人的心理调整、饮食营养、心身锻炼、生活指导等基本的康复知识、技能和方法。
北京大学肿瘤医院
返回
顶部
网站导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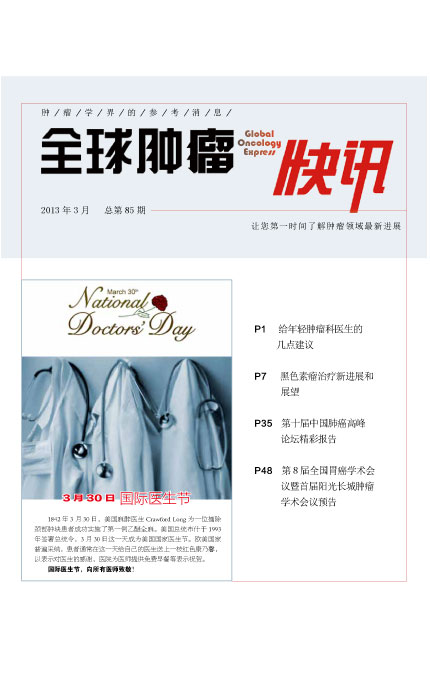
给年轻肿瘤医生的几点建议
作者: 来源: 发布时间:2013-10-11
年过八十,从事肝癌研究40余年,盘点人生,感到“人的一生,不在于做了几件事,而在于做成几件事”。我常说,一生做了两件半事,如果严格一点,恐怕只有一件事,就是“肝癌的早诊早治”,即使这一件,也是我们团队集体努力的结果。
由于早诊早治,肝癌已从不治之症变为部分可治之症,我们研究所住院肝癌病人的5年生存率已从1960年代的4.6%提高到近十年的42.1%,这个进步完全是由于小肝癌手术切除比例的增高。然而小肝癌手术切除的5年生存率在过去40年间没有看到进一步的提高,始终徘徊在57%左右,瓶颈在于术后的癌转移复发。
至今,各种实体瘤的总体5年生存率超过50%的仍寥寥无几,发达地区只有大肠癌、宫颈癌、乳腺癌和前列腺癌;发展中地区则仅有乳腺癌和前列腺癌。提示癌症研究虽有进步,但仍然是一大片处女地有待开发。
随着我国经济有所改善,如何形成有中国特色的肿瘤医学便提到议事日程。所谓中国特色我以为主要是两点,一是结合国情能多快好省地治好病人,这就要有原创的理论和技术,需要辩证思维,包括中西医结合;二是有崇高的医学人员形象,这需要有魅力、亲和力,为世界病人所向往。当前振兴中华的光荣使命已落在年轻同道的身上,我预祝大家在发展有中国特色的肿瘤事业中做出更大贡献。我想对年轻肿瘤医生讲三点:
一.一分为二看待事物
现在肿瘤临床实践中应用的几乎都是来自西方的东西,对于西方有用的东西我们固然要学习,但也要有一分为二的思维,尤其是我们所从事的专业,切忌偏爱。不仅要看到本专业治疗的疗效和优点,也要看到相关的副反应以及“反作用”,因为任何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这种例子无处不在,例如砒霜(三氧化二砷)是毒药,但也是治疗特定类型白血病的有效药物。
(1)一分为二地看待消灭肿瘤疗法:近百年来在抗癌战争中,发展了不少旨在杀灭肿瘤的疗法,取得了值得肯定的进展,可以说20世纪临床抗癌之战就是一部消灭肿瘤疗法的历史。但手术、放疗、化疗、局部治疗等,既有“正效”也有“反效”。“正效”大家都看到,不然就不会去使用它,但人们常忽视“消灭肿瘤疗法”的“反效”。我们在最近几年的实验研究中,发现这些疗法由于导致缺氧和炎症等,引起上皮-间质化(EMT),最终常促进残癌的转移,这个EMT的过程常伴有一系列基因的改变。例如我们发现放疗可促进远期残癌转移,和上调TMPRSS4这个分子有关。有兴趣的是,我们发现临床上经常用的一些“无关”药物,如防治心脑血管疾病的阿司匹林、治疗病毒性肝炎的干扰素,这些药物通过抗炎的作用,可一定程度减轻消灭肿瘤疗法的“反效”。我们发现一个含5味中药的小复方“松友饮”也有这种作用。一分为二地看待消灭肿瘤疗法并不是去否定它,要正视这些问题,并找到解决的办法,我以为这是提高现有疗法疗效的捷径。
(2)一分为二地看待分子靶向治疗:分子生物学的研究已到了收获期,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分子靶向治疗,它已经成为化疗后又一个里程碑。但越来越多文献提示针对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EGF)的靶向治疗促癌侵袭转移,停药后肿瘤又迅速生长(Lancet Oncol 2010)。我们的实验研究也提示,公认对晚期肝癌有延长生存期作用的索拉非尼,也同样可促进残癌的转移,其机理和索拉非尼引起的炎症(如巨噬细胞)反应有关;而用于治疗癌症骨转移的唑来膦酸,由于能清除巨噬细胞,如果和索拉非尼合用,可提高疗效(Clin Cancer Res 2010)。
(3)一分为二地看待免疫力:以前认为提高免疫力总是好的,但近年认识到免疫有双重作用,在纪念美国抗癌战40周年之际,2011年的《科学(Science)》出了一个专辑,其中的一篇文章指出免疫的双重作用,即既有保护宿主作用,也有促进肿瘤作用,临床需要综合考虑。回顾我们早年使用卡介苗的足三里穴位皮内注射,的确看到有些病人的病情好转,而有些病人则恶化。
二.抓住重点形成特色
我年轻时感到无所不能,但年过八十再回顾一生,感到如果能做成1~2件新的对病人确实有用的事情就不错了。人的精力有限,一定要抓住重点,才能形成特色。我以为重点应该是主流范围内的1~2个方向,切忌面面俱到,更忌见异思迁。面面俱到便没有重点,见异思迁就无法持之以恒,浅尝而止就难以形成特色。世博会我看了多次,印象最深的是英国馆,因为它只突出“种子”一样东西。这里举两个我亲历的例子加以说明。我们有幸获得两个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同样是抓住重点形成特色的结果。
40年前我从事肝癌事业之初,肝癌是“急转直下的绝症”,原因是病人就诊太晚,因此“早诊早治”便是关键,但文献中没有找到任何有用的线索,于是我们全所围绕这个重点,反复实践,反复修正认识,一干就是十几年。首先将国外发现的甲胎蛋白,通过检测肝癌高危险人群的血,然后长期随访,发现肝癌有一个较长的无症状(亚临床)期,提出“亚临床肝癌”是治疗肝癌的最佳时机。根据对肝癌高危险人群多次检测、随访和手术验证,发明了单纯用甲胎蛋白动态曲线来诊断无症状的小肝癌(那时没有超声显像,也没有CT)。接下来我们又提出以局部切除代替肝叶切除治疗伴肝硬化的小肝癌,从而达到既切除肝癌,又使手术死亡率降低10倍。最后一关是解决了用再切除治疗亚临床期复发转移,从而提高了疗效。这些临床改革的结果,最终使肝癌切除后5年生存率倍增(小肝癌为57%,大肝癌为31%),救活了大批病人,获得一条过去教科书从未见到的生存率曲线,并在国内外推广。当年这些因为国外没有,而我们有,所以被收录在几本最权威的国际专著中。国际肝病学奠基人Hans Popper认为“亚临床肝癌概念是人类认识和治疗肝癌的重大进展”,为此获1979年美国金牌奖。据了解,当年因为未能解决术后复发转移的问题,国内很多研究单位纷纷下马。我们如果未能始终抓住这个重点,未能持之以恒,就不可能形成特色,获得成果。值得一提的是,这个选题是从临床实际需求出发的,而不是从文献中去找的。
20年前针对癌转移复发是进一步提高疗效的瓶颈,围绕这个重点,我们又全力以赴,单是建高转移细胞系,就经历了78次失败,终于用12年的时间,参照逆向思维(过去癌转移的“种子与土壤”学说,认为种子需要合适的土壤才能生长,而我们发现不同的土壤也可影响种子的特性),建成世界上至今尚无的高转移人肝癌模型系统,解决了研究癌转移的平台,筛选出对转移有预防作用的药物,例如应用这个模型发现干扰素有预防肝癌切除后癌转移复发的作用(Hepatology 2000),经临床随机对照研究证实,已使病人受益。这个模型已在全球包括美国、英国、德国等近两百科研机构推广。我们在肝癌转移方面的研究也因此受到世界权威专著的认可,收录在癌转移研究权威Welch等主编的《癌转移:生物学背景及其治疗(2011)》以及美国国立癌症研究所Wang等主编的《肝癌的分子遗传(2011)》专著中。上面两个例子提示,一个阶段只能有一个重点,持之以恒,坚持十几年,才有可能形成特色。我曾经计算,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每个需要13年的时间。
当前医学文献浩瀚,光是您从事的专业,不睡觉也看不完。为此就要思考当前癌症临床研究的重点是什么,我个人认为主要有四个方面:(1)早诊早治——这是过去、现在和可预见的未来提高疗效的关键,由于甲胎蛋白阳性只占肝癌的半数左右,需要寻找甲胎蛋白以外,能够多快好省地早期诊断肝癌新的生物标志物。(2)综合治疗——因为癌症是多基因参与、多阶段形成,包含多个环节的复杂疾病。例如我们曾发现肝癌转移至少和153个基因有关(Nat Med 2003),针对一个或少数几个基因的分子靶向治疗显然不够,需要研究多靶点的治疗。为此综合治疗是治疗癌症的必由之路,是癌症研究的长远战略方向。综合治疗有两个含义,一是根据不同的病型和病期选用不同的疗法,二是对癌症采用多种不同疗法的综合和序贯应用,后者更为重要。过去的综合治疗模式是“消灭+消灭”模式,如术后加放化疗;今后需关注“消灭+改造”模式,如术后加免疫、抗炎治疗等。(3)改造残癌——这是提高现有疗法疗效的突破点。我们不但要消灭肿瘤,还要重视改造那些残余的肿瘤,一味采用消灭肿瘤的办法已经证明未能完全解决问题,两条腿走路总比一条腿走路要好。为此要探索免疫、抗炎、分化诱导、中医中药等可能改造残癌的办法。(4)癌转移研究——癌所以不同于良性肿瘤,主要是癌能够转移,这是攻克癌症的核心所在。现已认同癌症是全身性病变,为此需关注癌转移的全身性干预。大家如果认同,不妨在这几个领域找准自己的位置。
三.融汇东西创新学派
美国一位教授曾说“谁把握了东西方两种世界观的长处,谁就会在21世纪获得最大成功”。2011年1月10日《文汇报》也在头版头条刊登了我的文章“融汇东西方思维精髓,走中国特色创新之路”。作为中国人,我提倡中西医结合抗癌,因为二者如同硬币的两面,可以互补。例如:微观与宏观,局部与整体,单药与复方,消灭与调变,看肿瘤与看病人,一病一方与辨证论治,以及思路上由机理到应用和由实践到机理等等都是可以互补的。西医在消灭肿瘤方面有优势,但整体观略欠;中医消灭肿瘤力量不如西医,但改造残癌和改造机体有优势。
随着系统生物学的进步,西方对整体的调控也受到关注,整体观的信息明显增多。例如神经系统在癌症发病中的作用:体液和神经通路将癌细胞的信息转达大脑,大脑随后可通过神经、内分泌、免疫系统对肿瘤生长作出调节(Lancet Oncol 2010)。
癌症免疫治疗也有了新的进展:例如新的抗体为基础的免疫治疗是针对免疫细胞提高其抗癌免疫反应,而不考虑肿瘤的抗原(Cell 2012);有些分子靶向药物如伊马替尼,其抗癌作用是通过免疫刺激(Nat Med 2011);主动免疫治疗是癌症病人获得持久疗效的途径(Nature 2011)。
通过全身的代谢干预研究已成为热点。民间有一个说法是癌症病人不宜吃得太好,现在确有报道,认为ATP消耗促癌代谢(Cell 2010)。过去认为营养不良和癌症有关,而现在肥胖也成为癌症的危险因素,有报道肿瘤细胞代谢与分解脂肪有关(Cell 2010)。还有报道,肝癌增殖主要与糖代谢相关,而非血管生成(J Hepatol 2011)。我历来不主张癌症病人用氨基酸,因为20年前我的博士生已发现氨基酸有抑癌的也有促癌的,其中精氨酸有抑癌作用,最近已有报道,长效精氨酸脱亚氨酸可使晚期肝癌病情稳定(Brit J Cancer 2010)。分子生物学的研究也同样紧密与代谢挂起钩来,有报道“全身PTEN水平升高可导致较正常的代谢状态,有助细胞避免癌变。它通过调节P13K通路,调控开关,抑制肿瘤细胞最显著的两个代谢特征-谷氨酰基和Warburg效应”(Cell 2012)。
当前抗癌战略的争论亦已悄悄掀起(带瘤生存还是消灭肿瘤)。所有这些也说明中西医结合可能是抗癌战的一条出路,我并不是说大家都要去学中医,去开中药方子,但要关注中医的一些重大理论和视点,尤其是整体观和辨证论治,后者是整体基础上的个体化治疗,如果与当前分子基础上的个体化治疗相结合将更为全面。